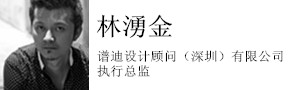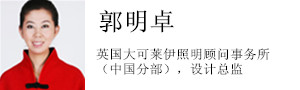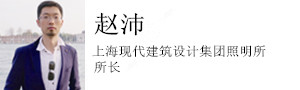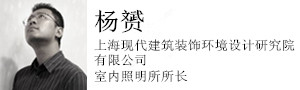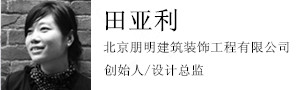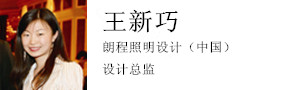依照以往所获知的人类发展史可知,人与动物最为重要的区别就在于人会制造工具。这一点作为一种人类社会普及性的知识早已经获得了最为广泛的认知,然而,随着人类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程度不断加深,有关人与动物之间因“制造工具”而呈现区别的说法也逐渐需要加以补充:
首先,是“制造”的概念需要完善
“制造”是一个特指,是指对于前所未有的产物的生产制造,其中包含着极为显著的原创和独创,并不意味着简单的“器物复制”或“依照现有的样板进行批量化的生产”。应该说,“制造”的本意在人类设计实践不断进行的过程中逐渐被淡化直至完全消失,这个从“产生”到“淡化”直至“消失”的过程,也就是设计逐渐从“与器物制造一体”到逐渐成为一个“独立的实践门类和行业”的过程;其次,是“设计”与“制造”之间的关系要明晰
仅仅是“制造”尚不足以成为人类区别于动物的根本性要素,因为就产物的产生来讲,“制造”这个环节已经是一个中间的部分,而“谋划在先”的“设计”才是最初的源头,即如当代社会所倡导的“先进制造技术”,就是在“制造”这个点上将这种主次关系进行了明晰。对于人与动物的差异性来讲,“设计”才是根源。围绕设计所展开的制造并由此产生的产物才是人类所独有的,也才是人类社会存在与发展的立基。
由上述两个方面,我们不难形成这样的结论:“制造工具”这一概念本身,含有相当比重的“设计”的成份。工具,实际上是人类意愿的延伸与发展。这样的一种认识形成,非常有助于我们了解早期的人类。人类的早期,以肉体来与环境相协调、相沟通,显得极为被动和弱小,常常成为各种兽类的食物。然而人类极具主动性的设计行为使相应的实践充满了和目的性,这注定了人类不可能长久地处于这种被动状态——通过充满设计色彩的实践,在事实上不断重新调整与自然的关系,从而以一种主动的姿态来促进自身在自然界中的发展,这成为“人类发展史”的主线。
对于处在混沌时代的人类真实情况的探究,不仅是会令人感到新奇,同时也显现出设计发展的一种必然路径,而这一点也是广义的“设计传统”探究的重要依据。在那样一个久远的时代,先民们究竟是如何来实施上述行为的?
首先,观察包含动物、植物、气象在内的一切自然现象
这其中没有哪一个是最重要或最次要的,对于当时的人类来讲,它们处在人类认识的相同层级。即使是在今天,在关于自然现象与人类关系的思考方面,自然之物的不同类别依然不构成思考时主与次的依据。这可以说是体现在人类思维之中的一种传统痕迹。在实践中,原始人不断对自身和自然中的各种自然之物加深认识,并将这种零散的认识做一定范围和对象的传播与交流,使之逐步成为“群体共性化”的认识,之后作为“知识”加以积累,并逐渐明确了自己的不足,例如,不能像兽类那样凭借尖锐的牙齿来“咬杀”对手;没有“猫科”和“犬科”动物的奔跑速度;也没有锋利的“爪”以击打猎物。但是原始人有日趋进化的手和日益发达的脑,于是,客观的自然之物的优势成为人类“自我保护目的”达成的重要参照:加工的器物表面的光滑、均匀,器物前端的尖锐与锋利,都可以或多或少地反映出工具(武器)加工过程中由对手见诸视觉的一些优势所获得的关于形态的启发;
其次,由上述认识深化为对于物质素材的有效选择
在材料的选择上,可以肯定的是:石头不是人类最初工具加工唯一使用的素材,可能也不是最早即有意识将“工具”概念与之对应的素材。当时的人类思维水平很低,还不可能以绝对化的认识去分门别类地看待周围的环境,也不太可能对于构成环境的诸多元素做哪怕是一些极简单的分析,他们对于周围种种可视的物质所采取的态度,是完全的“拿来主义”——先拿来用,如果不合用就予以淘汰。这种做法,是以实验性为前提的,在不断地实验之中,选取适宜的素材,加以一定程度的推广,(传说中“神农氏尝百草”的故事,在一定程度上正是说明了这种情况)。在此基础之上,人类由最初完全源于偶然的做法,而逐步在一定的阶段演化为必然性的自觉行为并达成相应的目的——首先就是逐渐选择到了适宜于自己使用的制造工具的素材——既有石质的,也有骨质、纤维质和木质的,这可以在对一些文物的情况分析之后得到证实:当人类通过对于周围的种种物质进行偶然性的尝试之后,逐渐将“工具”的概念,与几类物质相对应:用手难以打杀野兽,但凭借石块就容易得多,用双手敲击硬物,往往会伤害自己的手,而应用石块加以解决就变得轻而易举,因此对坚硬的石块进行加工,弥补手的不足;另外,原始人将树枝做成投枪和弓箭,通过投掷,使投枪、弓箭能够追上疾速奔驰的兽类并将其刺中,这样既保证了自身的安全,又获得了食物,提高了捕食行为的效率。此外,原始人类在风餐露宿中已意识到居住的条件影响到自身的生存,于是先“穴”居,后“搭窝”,逐步形成了“居有定所”的生活方式。这一切都是极富设计意味的工具制造行为。在种种设计行为的实施过程中,人类对于材料本身的了解,跃上了新的台阶,工具的概念随之不断呈现扩大化的趋势,生活质量得到提高。
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从某种意义来看,就是不断寻找新的素材,并将其转化为满足人类种种需要的工具的历史。物质材料被发现、利用的本身,就体现了一种实质上的设计含义——将本无任何意义的天然之物,赋予了极具实用性的工具素材的内含,这是物质本质上的转变,是人的意识得以一定的物质化体现的标志。所谓人类的设计行为,由此开始变得具有了一些初步的秩序感和层次感,逐步摆脱了最初由素材寻找阶段即出现,并伴随设计行为全过程的盲目性和偶然性。如果没有这些富有设计意味的工具制造行为,人类绝不可能发展到今天。因此,缺少设计意味的工具制造乃至其他的设计行为,不会对人类的发展有所推动和帮助,即使被制造出来,其生命力也是相当脆弱的。
再次,“功能”成为实践追求的唯一目标
从历史上看,设计在古代是包含在物品制造这种行为中的,仅仅是制作者的一种意识而已。对于原始人类来讲,这一点更应是极为真实的一种状态。当时的人类在制造产品的时候,由于思维的简单化,对于产品的功能以及形式都只限于简单的认识之中。尤其是形态方面的要素,更是近乎随意,根本谈不上什么精益求精。以“用”为前提产生的“物质功能”是绝对化的,不太可能具备多少以“欣赏”为目的、为满足视觉感官的愉悦而考虑的、外观的修饰成分,因此,仅就“功能”与“形态”的关系而论,在当时的那个阶段,形态仅仅是一种伴生物,仅仅是为满足“用”的需要,而无法摆脱的一种(物质)功能的载体,本身并不具备多少“独立”的含义。即便在形态方面有不同以往的创造,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在使用过程中对产品的功能有了新的需求或发展而产生的“要求产品必须具有与之相称的形态,来体现产品所具有的适用性”,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影响到产品的形态——早期人类使用的盛装器皿,先是底部如锥体的尖端一般,可插入土地中,以求得稳定(这一做法也许源于尖锐的石块,可及其轻易地穿透目的物这一现象);或在取水的过程中,便于快速方便地将水充满容器。可是在保存容器中的水的过程中,又发现这一形态本身的不稳定,由此,现实经历告诉人类:以器皿尖锐的底部来求得稳定只是瞬间的,只有重新改变器皿的形态,才可以长久地保持盛装器物的平稳。于是主流化的平底或圈足的盛装器皿就会大量产生。
人类社会的进步,要求人类无论是生产或是其它方面的实践,都必须时刻带有创新意识,而“创新”的根本理应是建立在对于实践构成成分的理性认知和辩证分析的基础之上的,从本质上来讲,所谓的“创新”就是不断对于构成实践的诸多要素进行最佳的组合。这就意味着,人类社会不同阶段的设计创新,就是从构成产物的素材到具体产物本身的形态,以及促使产物产生的制造方法,都在不同的阶段以在当时看来堪称“最佳”的组合方式得到的完整的体现。不同阶段最终成型的种种产物,一方面给我们提供了关于人类创新意识不断发展的清晰的轨迹,另一方面,为我们现实地诠释着什么叫“创新”。就本源来看,人类共有的“在自然环境中更好地生存和发展”这个目的堪称最为本质的硬核。这一硬核从古到今乃至将来,都不会改变。因而,以挖掘人的潜在功能并使之得以延伸以及借鉴自然环境中种种生物的优点,为人所用为目的的饱含创新意识的设计行为,也势必会伴随人类的出现而产生、人类的进步而发展,始终成为人类观照自身思维与行为的镜子。
高兴博士简介

高兴,博士,兰州商学院艺术学院副教授,无锡太湖学院客座教授。先后获得江南大学文学(设计艺术学)硕士学位,江南大学工学(产品系统设计及理论)博士学位。
现为中国设计师协会(CDA)理论委员会副主任,中外视觉艺术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外美术研究院理事、研究员,中国流行色协会拼布色彩与艺术研究专业委员会委员,成都蓉城美术馆学术主持、特邀评论家。
出版有《新设计理念》《设计概论》《设计伦理研究》《设计问道》等专著7部,在《甘肃社会科学》《西北师范大学学报》《甘肃理论学刊》等CSSCI刊物及核心刊物发表论文30篇,EI及ISTP双检索论文2篇,ISTP检索论文3篇。2012年荣获首届中国当代美术文献奖; 2014年荣获第十四届中国世纪大采风“中国当代最具影响力人物”称号。